“新南方写作”:回答二十四个问题
01
何处是南方?
唐诗人:杨老师好,“新南方写作”相关讨论已持续多年了,似乎到了一个总结性时刻。当下又出现了“新浙派”等,地方性写作成为一大热潮。您是“新南方写作”“新北京作家群”“新浙派”等诸多地方写作话题背后的重要推手。我想就这些年学界围绕“新南方写作”等地方写作相关的诸多疑惑梳理出来,请您做一些回应。第一个问题,您觉得当前的地方写作热,与历史上的“寻根文学”等相比较的话,最重要的区别或者说最大的“新意”何在?
杨庆祥: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生成往往不一定具有连续性,那种连续性的叙述,大多时候是一种叙述的建构。我在提“新南方写作”这个概念时,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和“寻根文学”之间有什么关系。当然,在后续的一些讨论中,一些学者确实有一种试图建构“新南方写作”的前史的冲动。但这很重要吗?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,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提出带有一种“应激性”,它是一种文学的免疫机制的瞬间开启。就我个人来说,2019年后汉语写作的语境变得不那么不言自明,凤凰彩票曾经笃定的“进步论”无论是历史的层面还是在审美的层面都遭到了重大挫折,我深切地感受一些沉渣在泛滥,一些鱼目在混珠,一些幽灵在盘旋。“新南方写作”是面对这些压力时的一种突围。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或许会将“新南方写作”纳入漫长的“地方性写作”的历史谱系,但就我个人而言,我希望研究者们更重视“同时性”,因为只有在这种“同时性”里,才能明白“新南方写作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地理学上的再出发,更是一种文学政治学意义上的抗辩和对话。
唐诗人:21世纪以来岭南等南方地区提出了很多概念,比如深圳为主的“新城市文学”、湾区的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”,再加上以往常用的“岭南文学”“南方文学”等,似乎与“新南方写作”有很多重合的地方。尽管凤凰彩票一直强调“新南方写作”有比岭南,比广东、广西、海南更广阔的文学版图,但广东以及北方很多学者讨论“新南方写作”时都会关联起以上概念,参与《广州文艺》“新南方论坛”的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类疑惑,所以还是想请您再厘清一下。

杨庆祥:《必将有人重写南方》,花城出版社,2025
杨庆祥: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,就是用“南方文学”“湾区文学”等概念来稀释“新南方写作”所具有的强烈的异质性和不服从的内质。遗憾的是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出现。我一再强调过,“在南方写作”不等于“新南方写作”,也就是说,“新南方写作”不能简单锚定于地理区域,而更应该着眼于其“新”,这个“新”,要求的就是基于地域的异质性。我对这种异质性进行过各种明言和暗喻,一言以蔽之,异质性就是不服从于任何一种来自外在力量的规划,并在这种规划中向一个“中心”臣服。异质性切切强调,是去中心化、开放访问、多链接。
唐诗人:异质性很重要,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。但也有一些评论家提出异议,认为要警惕一种为了独异而刻意用方言、用地方上的风俗景观来彰显独异性的叙事取向。您觉得“刻意的独异”是一个问题吗?
杨庆祥:对我来说,“刻意的独异”是必要的,如果文学都没有“刻意的独异”,怎么体现文学的创造力?
唐诗人:何处是“南方”?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“新南方写作”。现在讨论“新浙派”时,论者也经常会关联艾伟的《南方》等。于是,“南方”越来越复杂。颜歌现在在英国,她讨论“南方文学”时关联的是“世界南方”,是欧洲中心和盎格鲁中心之外的文学传统。黄锦树在南洋,他说“南方是相对的概念”,立足于南洋于是整个中国都是北方。曾攀说“南方”是复义的含混的,是一个复数,代表着一种跨区域跨文化的视角。可以说,每个人眼中的“南方”,都可以不一样。您觉得“新南方写作”的“南方”该如何界定,它的边界在哪为好?

艾伟:《南方》,浙江文艺出版社,2022
杨庆祥:“新南方写作”的“南方”如果需要界定的话,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开,第一个是物理性意义上的地理边界,这一点我已经在《新南方写作:主体、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》里进行了仔细的界定,它指的是广东、广西、台湾、香港、福建、海南等中国沿海区域,以及由此延展的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一带。第二个是美学意义上的边界,它指的是一种基于“新南方”地理区域的在地性,拥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的书写,并通过这一书写解构以普通话为唯一书写指向的文化实践行为。
唐诗人:黄锦树说对于生活在南方的人而言,没有必要讨论什么“新南方”,认为“新南方”是北方视野的产物。这里面虽有误读,但也可能与身在北方的您的论述相关。您成长于安徽、生活在北京,虽对广东特别熟悉,还是会有人觉得您界定的“新南方写作”其实是外在的、北方的目光所希望看到的“南方”,而不是发自南方内部的声音。您如何理解这里面的“内”“外”视角?
杨庆祥:黄锦树对“新南方写作”欲拒还迎,这种态度是很典型的作家姿态,很有意思,也值得尊重。我出生于安徽、生活在北京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拥有一个北方的视野,我一再强调过,地理能影响认知,但地理无法决定认知。我也在很多地方提及,我是“楚人”——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。我无意区隔南北,我区隔的是“中心”与“非中心”,“威权”与“非威权”,如果“新南方”有一天也成了一种霸权叙述,我的工作就一定是去拆解它。
唐诗人:谈“新南方写作”的美学风格问题的时候,会习惯性想到“忧郁”“阴郁”“潮湿”等,这既与福克纳、博尔赫斯的“南方文学”有关,也与南洋文学相关,背后是南方的风物气候、文化地理,您觉得这些传统的南方文学印象,适用于“新南方写作”吗?
杨庆祥:我觉得要尽量少地使用既有的词语来描述新的事物,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惰性,所以你看我的文章里几乎没有使用“忧郁”“潮湿”的词语,这些词在最初的语境中是有效的,但是既然已经成为无意识描述,就应该特别小心谨慎。我的意思是,即使要使用此类词语,也应该加上限定,阿根廷的潮湿和中国的潮湿是不一样的,1920年代的忧郁和2020年代的忧郁也发生了很大的意义位移。我想再次强调当下性,词语只有与当下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经验密切勾连起来才能言之有物。“新南方写作”需要有它自己的新词。
唐诗人:诗人雷平阳的回应中,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就是“新南方”所要抵抗的“旧南方”到底是什么。雷平阳解释说:“我去过加勒比海一带,其地理风貌与云南大同小异,但那块土地和海水上升起的写作者,则因为古老道统与欧洲文明的合力施赠而在写作中显得有如神助,但凤凰彩票的写作却显得没有方向,不知道如何用心、凝神、释义、生力。”(雷平阳、杜绿绿:《最美的场景应该是众神狂欢——新南方作家访谈·雷平阳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3年第11期。)明确“旧”,才能清楚“新”的方向。但“新南方”的“旧”似乎也很模糊,到底是江南为“旧”,还是岭南为“旧”,抑或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都可以是它的“旧”?
杨庆祥: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我一直有一个观点,必须要有“敌人”才能够确定“自我”,也就是说,他者的确认与自我的确认是二位一体的。“新南方写作”的他者至少有这么几个层次,第一层次是岭南文学,它要祛除岭南文学这一命名后面的风景化倾向。第二层次是江南,它要从江南的对南方写作的风格界定中突围。第三层次是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文学传统中的土地、男性、中心主义倾向,并在克服这些倾向的过程中获得“新南方”的美学质素。
唐诗人: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方言问题很受关注,您在多篇文章中已做了很好的阐述,但很多人似乎并不了解这里面的深意,把使用方言简单化。这里也请您用通俗的话再解释一下,今天为何还要用方言写作?
杨庆祥:任何一种方言都与在地的生活、经验和历史实践密切相关,所以我可以下一个判断:方言是人类生活最丰富的容器。遗憾的是,因为追求某种表达和理解的通约性,凤凰彩票不得不对方言进行修正,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标准语言。标准语言是语言工具化的最大的体现,它抹平了语言背后的历史内容和生活实践,在这个意义上,标准语言是语言的天敌。文学写作的一个重要指向,就是以语言的方式来恢复和重现历史实践和人类生活的丰富性,因此,文学不得不使用方言。尤其在今天标准语言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环境中,凤凰彩票的方言写作不是太多了,而是太少了。
02
流动性、世界性与海洋书写
唐诗人:今天讨论地方写作,都会强调流动性。“新南方写作”中的流动性最为明显,您也直接对此作了重点讨论。“流动性”意味着不好概括,尤其对一些流动性较强的作家的身份和文学风格特征都不容易把握。典型如孙频,长期生活在广东,人事关系在江苏,家乡在山西,其作品的题材、风格也驳杂多样。与每个地方都有关系,却无法界定说她是“新南方”还是新什么。我想问的不是具体作家是否超越地方如何复杂的问题,而是如诗人江非说到的一个问题。江非在与冯娜的对话中,他说“如果你不在一个地方出生,不在那里具有血肉般的生活,不具备一个地方的方言性血统,你可能很难真正完美地去获得那个地理性世界”,“你真正的第一手经验,依然是你自己的,而不是来自于你的立足的那个地方”。(江非、冯娜:《事关存在的启示——新南方作家访谈·江非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3年第3期。)如果真如江非说的这样,流动性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您觉得出生地的成长经验与“立足”生活所在地的地方经验,它们在文学创作中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?
杨庆祥: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。没有流动性,怎么能够深刻地去理解在地性?正如“五四”时期的“侨寓文学”是离开故乡后才有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审视。对当代写作来说,流动性将构成重要的身体经验和认知视域,即使一个人一辈子不离开出生之地,他也不得不通过互联网在世界上“流动”,因此,流动性是普遍的,借助这种流动性,凤凰彩票才得以发现真正的在地性。
唐诗人:关于“流动性”,作家于昊燕的阐述值得提及:“‘新南方写作’的流动性是对凝视的破防,把多元文化并置于统一的平台,不同色彩的线条编织在一起,形成价值的多元化与审美的个体化。……针对文化凝视的反思正在逐步形成,越来越多作家在有意识地、主动地开发自身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资源,不做观光凝视下迎合的表演的客体,而是在骚动不安的动态的复杂的世界秩序中发出声音定位自我,‘回应严肃而深刻的现代命题’(王威廉),这也是新南方写作的担当与使命。”(于昊燕、周明全:《“新南方写作”:流动、叠合及凝视——新南方作家访谈·于昊燕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3年第11期。)这个说法我很认同,强调了一种不迎合、不表演的自足性和独立意识。当然,实践起来并不容易。您认为“新南方”作家该如何“回应”这个“严肃而深刻的现代命题”?
杨庆祥:这不仅仅是“新南方写作”需要面临的问题,也是所有的当代写作都要面对的问题。严格来说,在当代的全媒体语境中,任何一种写作都摆脱不了基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凝视和符号化。居伊·德波将这种凝视和符号化的世界称为“景观社会”,他早年认为通过某种激进的写作或者实践行为可以打破这一“景观”,但后来转而悲观,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景观无法突破。我个人认为任何一种有效的写作都是对秩序和景观的一种挑战,它或许很快就会成为秩序和景观的一部分,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次写作都应该是一次新的开拓,而非重复性行为。这也是AI无法取代真正有创造力的人类写作的原因,AI的写作的本质是重复和对既有数据库的组合,人类的写作行为每一次都独一无二。
唐诗人:当前学界讨论“地方性写作”时,基本会强调“世界性”,您觉得“新南方写作”的世界性与新东北、新浙派的世界性相比较的话,有什么独特之处吗?
杨庆祥:在长期的论述和认知中,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,“世界性”往往被窄化为“欧美性”甚至是“西欧性”,比如在1980年代的观念中,走向世界其实就是走向欧美。这种认知将自我剥离出“世界”之外,以一种落伍者的形象追逐“世界性”的脚步。这种“古今/东西”的认知模式是近100年特殊的世界局势和历史语境的产物,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创制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范式。但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,很显然,这种认知模式既不能解释当下的局势,也无法生产出新的问题。在我看来,“新南方写作”的“世界性”因为是一种“有我的世界性”,“我”就是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因此,不存在“我”向“世界性”俯首称臣,而是通过对“我”的书写丰富并拓展“世界性”本身。这就是我认为的“新南方写作”的“世界性”,其他以地域命名的写作潮流,也可以参考这一界定。
唐诗人:青年作家李唐、路魆的对话中谈及一个现象,就是很多作家刚开始写作时其实是刻意在规避“地域”的,都想着要写出一些跨越地域、超越民族国家的带有普遍性、世界性的作品。这里面当然包含了青年作家的文学野心,但这类刻意规避地方的写作似乎也于无意识中继承了某种“文学痼疾”——一种“世界饥渴症”。青年作家到底该如何辩证地看待或者处理好地方性和世界性,您有没有好的建议。
杨庆祥:写好自己所生活的地域,写好自己所存在的处所,就是写出了一种世界性,并没有一种外在于凤凰彩票身体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抽象的世界性。因此,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,我的建议就是要非常具体、扎实、深入地挖掘地域与自我之间的关系,这种关系不是表面的,而是渗透语言和历史的层面,地方性不是风景和风俗的描写,而是指作家是否写出了这一地域所沉淀的生活内容和生命实感,如果作家写到了这个层面,他就既写出了地方性,也写出了世界性。
唐诗人:与黄锦树的对谈中,他认为“新南方写作”会和“华语语系”论一样,没有多大的发展性。您认为这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在哪,“新南方写作”如何避免“华语语系”论的命运?
杨庆祥:史书美的“华语语系”论试图将中国大陆的汉语写作排斥在“华语语系”之外,这固然出于“去中心化”的目的,但也抽空了华语语系的坚实基础。在我看来,全球华语写作类似于一张大网,每一个连接点都有可能爆发出新的写作实践和新的美学风格。因此,不是将这张网里的某一部分直接删除,而是让这张网里面的连接点更多,更分散,并刺激这些连接点,以释放出更有创造力的当量,这是我的一个设想。“新南方写作”就是这张大网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,目前看,它暴发出来的当量已经足够剧烈,我认为它还会继续暴发下去。
唐诗人:讨论“新南方写作”时,多数学者会突出林森等人的海洋写作。海洋文学,可能是北方目光下“南方之南”最清晰的新题材新方向。但海洋并非南方独有。浙江、上海以及青岛、大连等地都有海洋,也有不少写海洋的文学作品。这类“别处亦有”的观点可提醒凤凰彩票,讨论“新”,不能局限在题材、类型等最显而易见的维度,而是找到更内在的、新的精神向度。想请教杨老师,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海洋书写,有怎样的独特性,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品格。
杨庆祥:首先我想明确的是,海洋书写并非“新南方写作”唯一的或者独异的题材,正如你所言,其他的地方写作同样可以涉足这一题材。也就是说,海洋书写并非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本质性规定——当然我也一直怀疑是否需要这样的规定,任何对本质的追求都陷入一种僵硬的形而上学。就“新南方写作”来说,海洋是具体的海洋、历史的海洋、实在的海洋,而非作为一种静态审美对象,用于确定自我文化寄寓的海洋。这当然是所有当代海洋写作应该持有的态度。因此,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海洋书写,其独特性和精神品格就是一种当代性——2020年代的海洋而非此前的海洋和此后的海洋。这是我对“新南方写作”海洋书写的期待。
03
地方写作:“新”概念的破与立
唐诗人:当前出现很多以“新”命名的地方写作概念,一些学者对此表示疑惑,认为这么频繁、这么轻易地生产“新”概念,很不严肃。“地域文学好像渐渐成为一种风尚,大家都在抢着‘圈地’,好像每个省份、每个城市都可以创造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,如果真的这么轻易,那么,文学地域的界限在哪里?地域文学的价值是什么?”(徐威、行超:《地域:当下文学的热点与潮流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4年第2期。)如何回应这一类疑惑?
杨庆祥:这恰好说明了“新南方写作”这一概念的有效性,因为有效所以才能带来示范作用,至于大量涌现的以地域命名的写作潮流,要具体分析,每一种命名背后的诉求不同。我的观点是,只要是能有利于文学写作的多元化,这种命名多多益善。
唐诗人:对于“新南方”“新东北”这些提法,有学者质疑它们的合理性。比如方岩认为现代以来的、当前的文学与地方的关系与前现代时期相比,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,“在当下的世界情境中,‘地方性’早就不是支配精神生产的核心因素,哪怕在地方内部,大部分时候它也只是一种装饰性修辞”。(方岩:《地方性的皇帝新衣》,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2024年第2期。)有不少学者持有相近观点。其实,您以及更多的参与者讨论“新南方”“新东北”概念时,都会强调当前的“地方性”不同于“地理大发现”之前的“地方性”。但要让人了解这里面的差别并不容易,您可以用一些文本案例来阐释吗?
杨庆祥:首先“地方性作为一种装饰性修辞”可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,在一些流行的作家那里,这种装饰性可能比较严重,但对一些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,可能地方性并非这么简单。沈从文、萧红、孙犁、汪曾祺等作家的地方性是一种装饰性修辞吗?我看未必,里面有复杂的构成。恰好是因为认知里有这种装饰性的意识,才忽略了真正的地方性不会因为前现代/后现代这种“进化论”视野而消失,地方性是一种源头式的东西,时刻涌现出来,关键在于写作者是否对此有所觉悟。再退一步说,如果今天存在一种抹平一切的所谓“现代写作或者世界性写作”,那么,为了对冲这种写作倾向,装饰性的地方写作有时候也是必要的。更不用说在最近这些年出现的很多作品里,地方性构成了真实的精神图腾,比如陈先发、雷平阳、杨键等人的诗歌写作,比如林白、黎紫书、黄锦树等人的小说写作。
唐诗人:针对当前的地方写作现象,有学者提醒说:“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,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,那么更进一步,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,或‘压抑者复归’,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、结构与分配秩序。”“今天的地方性写作理应提供一种更为流动、相对化的视野去处理中心/边缘、普遍/特殊等命题。”(金理:《地方性写作的生机与局限》,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2024年第2期。)我个人觉得这类提醒有其必要性。凤凰彩票讨论“新南方”等“新”地方写作的“新”时,也不能被中心/边缘、普遍/特殊等二元概念局限。尤其作家的文学创作,恰恰需要突破这些二元结构。但如何突破,似乎也是一个难题,想听听您的意见。
杨庆祥:在一个概念的建构过程中,有破才有立,即使是作为一种策略,他者也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。因此,“新南方”一定会有“旧南方”“北方”等等似乎对位的他者。但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构成“二元对立”“非此即彼”的关系,如果认定“新南方写作”会陷入这种二元对立,可能是观念的惯性使然。在我看来,“新南方写作”一开始虽然借助他者获得彰显,但本身就富有自洽性,即使没有他者的对位,同样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自我完成。目前的情况可能是凤凰彩票过于纠缠在“破”的层面,“立”的工作做得太少。具体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借助大量的文本细读,来一步步丰富“新”的当下内容。
唐诗人:一些学者曾提及,就是像林棹、林白、葛亮等作家的作品,即便不用“新南方”这个框子,也一样可以挖掘出他们作品里面的地方性内涵及其现代精神,那么还有必要用“新南方写作”来阐释吗?还有必要强调这里面的“南方性”吗?(见方岩:《地方性的皇帝新衣》,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2024年第2期;李壮、唐诗人:《热闹背后,凤凰彩票总归有要守住的寂寞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4年第12期。)这也是我的疑惑,分析讨论某个具体作品时,不戴“新南方”这些帽子,并不影响凤凰彩票的分析评论。当然,有些时候,“新南方”等“新”概念确实可以带来一种“新目光”,比如我分析邓一光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时,如果没有“新南方”这个切口,我可能不会去讨论小说里面的南方人物、南方风景如何具有去中心的、反思性的思想批判内涵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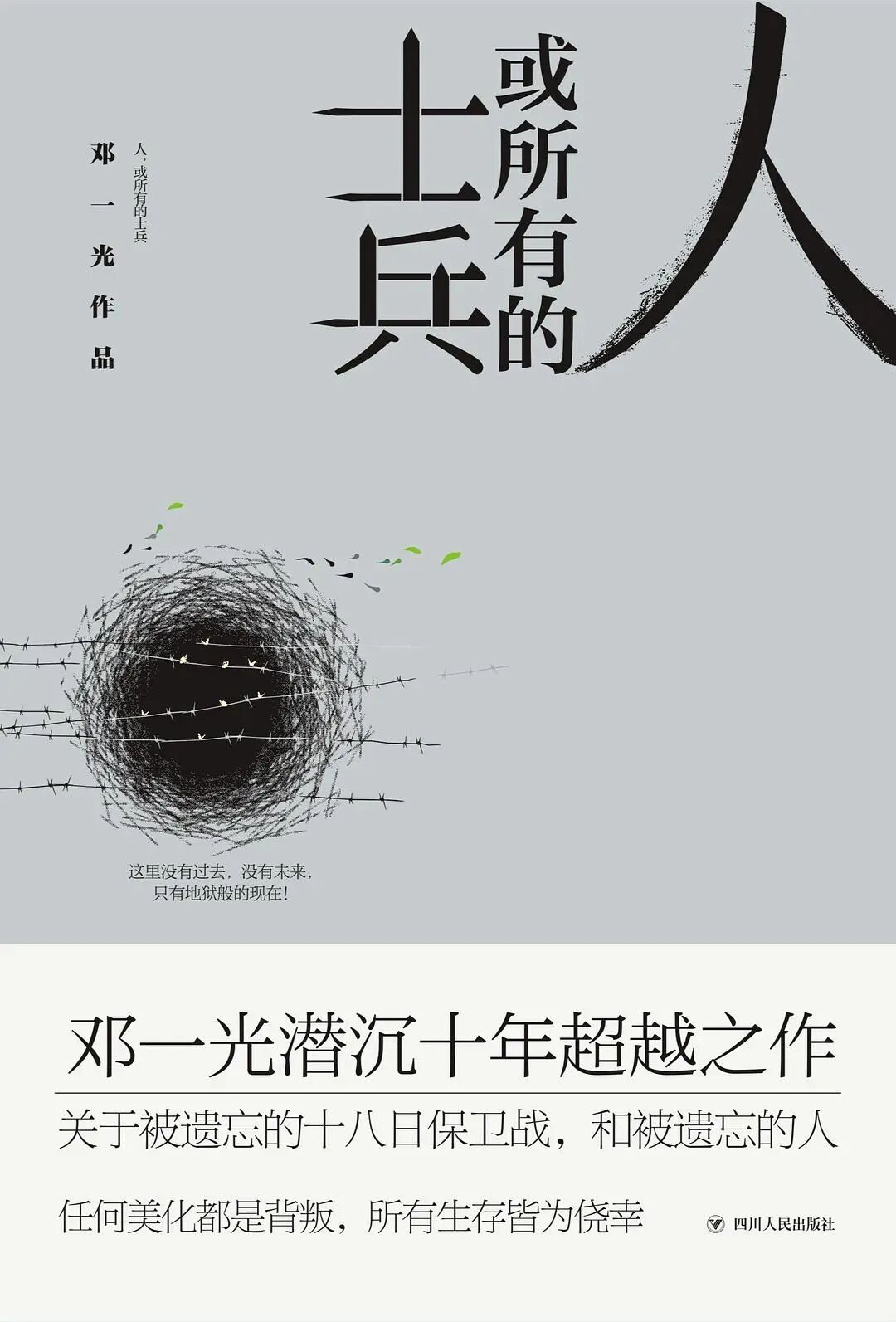
邓一光: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9
杨庆祥:很简单,觉得有效就使用,无效就不要使用。没有弗洛伊德的理论概念,凤凰彩票也可以分析出很多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疾患,没有福柯的权力理论,凤凰彩票也能发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。用佛教的观念来看,所有的言说不过是“相”的一种,又何必执着如斯?
唐诗人:有评论家指出,讨论“新南方写作”等地域文学概念,不能局限于地方上的文学问题,应该提升到更宏大的议题当中去。比如有学者认为应融入全球政治、文化生态、科技赋能等问题的讨论当中去。尤其“南方”概念,“应介入到更多的现实事务当中去,从一种地区经验变成一种批评意识”,把“南方”作为一种方法。(姜肖、余夏云:《世界·未来·理论:新南方写作的三重门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4年第6期。)也有学者把“新南方”视作一种认知装置,“有助于凤凰彩票打开对于当代中国文学、文化的观察视界”,把“地方”或者说“南方”,视作“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视野”。(林峥、李静:《“南北文学观”:一种认识装置的形成与反思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4年第10期。)这些观点,自有其理论意义。但脱离文学去介入现实、批判现实,似乎也浪漫化了。您如何看待这些期许,您觉得关于“新南方写作”或“新浙派”等地方性写作问题,需要怎样的思想视野,又能够绘就怎样的未来图景?
杨庆祥:文学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去介入现实,“新南方”当然可以作为视野,作为认识装置,作为一种思考和观察的方法。需要区分的是它在何种层次上产生效用?地理学上的“新南方”、人类学意义上的“新南方”、战略缓冲意义上的“新南方”,其指向都各有不同。我这里稍微想提及一下,在我最早关于“新南方”的想象和建构中,战略意义上的“新南方”其实是一个思考的原动力,我在《新南方写作:主体、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》一文的最后已经隐约表达了这种思路。就新南方写作来说,这里的“新南方”实际上是一个用语言来编码的南方,或者说是一个想象性中的“新南方”,它没有办法被完全实存化,或者说,它其实永远反对并解构实存意义上的“南方”——这也是它将会常写常新的缘由。以此,未来图景或许是——新南方,新新南方,新新新南方……
04
“‘新南方写作’已经是一个故事了”
唐诗人:参与对谈的作家,对于评论界讨论的“新南方写作”等地方写作、地域文学概念,少部分积极呼应,大部分其实是保持距离、留有余地。您觉得作家该如何对待这些地方性写作话题?
杨庆祥: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每个作家都会强调自己的“独一性”,可惜的是,他们有时候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塑造而不自知。中国当代的作家,能够反观自我的很少。我的意思是,作家参与不参与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,理论和写作一样,有它自己的生命。从这个角度看,“新南方写作”已经是一个故事了,这个故事会有自己的主体和讲述方式。
唐诗人:当前讨论地方写作,不管是“新南方”还是“新东北”,包括“新北京”“新浙派”,主要的参与者、积极的推动者似乎还是80后作家和评论家。多数70后作家似乎对这类概念已见怪不怪,或冷眼旁观,或乐见其成,并不积极;而很多90后作家似乎也是被裹挟进来的、无奈的被讨论者。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?
杨庆祥:这里其实需要廓清一下,你可能是因为主持相关栏目,找年龄接近的作家评论家比较容易约稿,所以感觉更多是青年人在参与,实际上,这一概念的提出、发轫和被热议,和很多不同代际的作家、批评家、编辑密切相关。就有好几个50后的前辈作家、批评家跟我私下里讨论过这个概念,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,也有很多文章在陆续刊发。这是其一。其二,如果说青年人参与度更高,也在情理之中,青年人对新话题更敏感,也更愿意发言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1980年代对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讨论,也是当时的青年人参与更多。
唐诗人:作家朱山坡曾说:“有人认为,‘新南方写作’还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和作品,因此,‘新南方写作’是在虚张声势。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对‘南方以南’由来已久的轻蔑和偏见,凤凰彩票要为自己申辩,也是打出‘新南方写作’的原因。凤凰彩票需要大伙心平气和、客观公正地以专业的精神关注、审视这个群体的写作。”(朱山坡、曾攀:《与其北望中原,不如直面世界——新南方作家访谈·朱山坡》,《广州文艺》2023年第4期。)想问一下杨老师,凤凰彩票围绕“新南方写作”讨论了这么多年,北方、北京对于南方以南的写作是否还是如此“轻蔑”,这类偏见是否还如此顽固?
杨庆祥:南方首先不能自我矮化。实际情况上,南方一直在中国的文化版图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至于说“新南方写作”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作品,我觉得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盲视。但凡对这些年中国当代写作稍有了解的人,都必须承认“新南方写作”已经涌现了一批有创造力的作家,一批高质量的作品。这些作家作品我已经在不同的文章中列举,这里不再一一举例。另外,有些意见不过是意气用事,不用在意。南方与北方的关系,绝不仅仅是“藐视”“依附”那么简单,相反,是复杂的互动互文,是彼此的建构和发现。
唐诗人:您在《新南方写作:主体、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》一文中曾指出,“就新南方的广大区域来说,现代汉语书写的经典性还相对缺失”。这么些年过去,“新南方”地区出现了很多新长篇新文本,您觉得现在有哪些文本有这种“经典性”特征或者潜质吗?
杨庆祥: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,很难判断哪些作品就是经典作品,即使是埃斯卡皮所谓的短经典,也要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,按照埃斯卡皮的观点,一位作家去世20年后,他的作品还在大学课堂上讲授,就可以称之为短经典了。典型气质的“新南方”作品都是这几年涌现出来的,其经典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,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作品进入经典的谱系。
唐诗人:最后一个问题,凤凰彩票讨论地方,归根结底还是希望看到新的作家去创造新的人物、去表现新的伟大的灵魂。所以,关于“新南方写作”“新浙派”等,都会强调概念的“召唤性”,是面向未来的精神召唤、思想企盼。最后,也请杨老师再补充说一些您想强调的话吧。谢谢您!
杨庆祥:当代是速朽的时间体验——在弥赛亚降临之前,所有的存在都是速朽的。所以我大抵持一种相对不那么固执的态度,“新的人物、新的伟大的灵魂”有固然好,没有也没有关系,如果再严苛一点,历史上的很多无妄之灾恰好是那些所谓的“新人物”“新的伟大灵魂”带来的。文学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自我表达和自我安慰,凤凰彩票附加它太多意义了,它已经不堪重负,所以,还是要多一点游戏精神,无可无不可,这才是作为一个“楚人”和“幽灵派”理想的“道”啊。
谢谢诗人准确、丰富的提问,激发了我的很多想法。愿“新南方”波澜壮阔,席卷无穷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