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执念》:生命的显影术
河西走廊上,古城墙仍在,青草萋萋,向历史深处漫溯。这里沉积着世上最厚的黄土,养育着厚重的灵魂。也孕育了无数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张晓琴深入甘肃腹地,足迹遍布河西古道,穿梭于祁连山隘和拉卜楞寺的经幡,广泛寻访百余位非遗传承者,深入记录唢呐、宝卷、皮影、剪纸、唐卡、贤孝、太平鼓等珍贵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,写就非虚构作品《执念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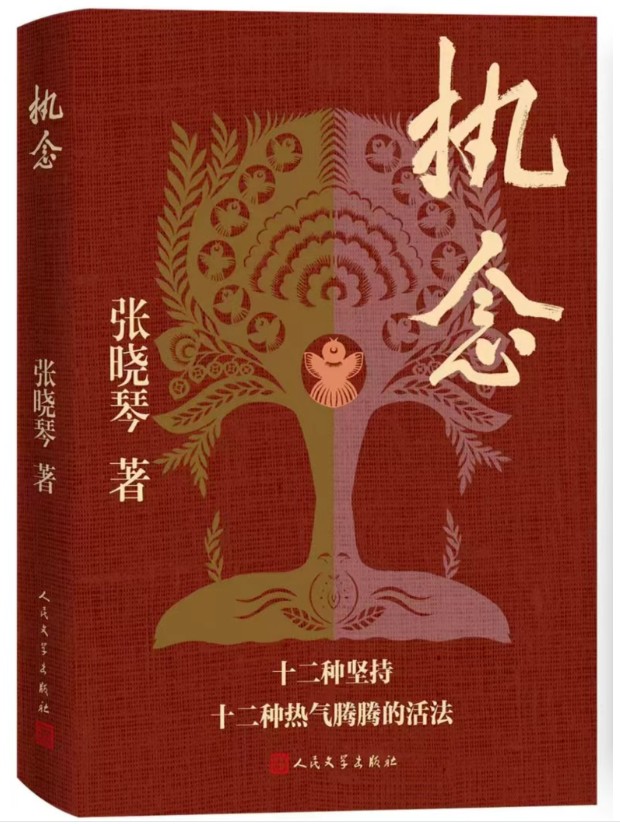
在《执念》之前,张晓琴的写作虽然兼涉各种文体,但从未如此整合地尝试大量口述实录的人物传记。《执念》由足量的采访整理、修改、重新书写而来。张晓琴对采访的使用在前作《大荒以西》和《一灯如豆》中已现端倪,这两种评论集在收录对杨显惠、陈晓明的访谈稿外,众多的评论中也可见到作者与小说家本人交流的痕迹,采访成为作者的一种治学方法。《执念》在结集出版前,发表在《十月》的代兴位篇体例还是访谈,随后刊登在《人民文学》和《飞天》写汪莲莲、徐宁的文章改而使用口述的方式书写。此种文体远推如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的《切尔诺贝利的祈祷》,近处则是同乡杨显惠的两本代表作。阿列克谢耶维奇意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外,书写与此有关的人物生平,“我想捕捉心灵的常态,普通人的日常生活”。同样,《执念》有意绕开了符号化的非遗,探察相关人物的生活细部,个人如何以一己之力托举一门技艺。
作家、诗人之外,张晓琴为人熟悉的身份是批评家和学者。张定浩写道,张晓琴的治学是“自觉认领一个熟悉亲切的研究领域,然后精耕细作,积土成山,积水成渊”,以数年之功“勾勒出一块属于自己的西部地图”。张晓琴与中国西部的关系其实在在可见。《执念》原名《非遗在我》。在,存也。《我与地坛》结尾史铁生写:“我已不在地坛,地坛在我。”中国西部存在于书中十二位艺人身上,也在张晓琴数年的写作中。非遗的认定、保护和抢救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,这中间往往更关注文化遗产本身,对传承人的状况难免关照不够。而文学则更关注人的生存、精神和命运,文学的价值也是在于对人的理解和关怀。从事文学批评多年的张晓琴体认到“非遗”二字背后可供索求的重心正是“艺”与“人”之辩,《执念》书写的是这些携带古老艺术的人,他们如何继承、处理、安放、拯救、光大恰好被各自所触摸到的艺术。
中国古代艺术以诗书画三绝为核心,有着强烈的文人传统,重精神、轻技艺,重人格、轻形似。诗人韩东说,凤凰彩票有文人传统,但没有艺术家传统,有艺术,但没有艺术家。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观点是没有艺术,只有艺术家。韩东的说法不尽然。在文人艺术的范围之外,大量传承古代技艺的艺人要以此为生,世代精进。《执念》中涉及的艺术门类远离文人世界,生发于社会底层,更具在地性和生命力。比如皮影、贤孝、宝卷、木偶戏的劝化,比如花儿对生活、爱情、时政、劳动的反映,再比如太平鼓、剪纸及香包所承载的节日欢庆。《执念》中频繁出现的是作者关于传承人人生的发问,观点接近贡布里希——有艺术家,才有艺术。《执念》中展现了三种艺与人的关系。一种是信仰以为生活,艺术即信仰,藏族唐卡、河西宝卷是历代传承人生命重要的一部分。交巴加布四年级辍学回家,一生中只做画唐卡一件事。代兴位父子在天灾人祸中冒死守护宝卷;一种是以艺术为生活,皮影、木偶戏、贤孝、唢呐是传承人讨生活的手艺。高清旺一家子都做皮影,许明堂在师父家吃住六年学习皮影;最后一种是艺术构成了日常的一部分,剪纸、香包、花儿、太平鼓、羊皮筏子,这些隐匿在生活中如同取水、节庆、祭祖。因为今天生活方式变化,观念变化,这些就成了一份不知如何安放的遗产。

太平鼓,图源网络
《执念》的书写是对生命的显影,作者的访谈和书写如同在暗室中成像,要求精准地呈现人物的生命状态。米开朗基罗言道,“塑像本来就在石头里,我只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”。对于有采访对象(原型人物)的《执念》,作者也要将不需要的部分准确地去掉,还原出真实人物。这种真实,并非采访对象本人所必然明白。张晓琴过去写道:“文学的真实并不等于现实,文学创作自然来源于现实生活,但文学创作的根本是虚构,是文字的行走,是面向人类的内心、人性,以及命运。”在对采访对象的深刻理解后,张晓琴得出的是“非遗在我”。汪莲莲唱的花儿是:“三股子麻绳背扎下,大堂里金柱上绑下。钢刀拿来着头割下,不死就这个唱法。”凉州盲艺人的贤孝唱词是:“咱们两个若要散,青冰上开一朵牡丹。”唢呐艺人马自刚说:“无论在哪里吹唢呐,我都觉得是在庆阳的黄土地上。”生命同艺术已是一体,我已不在非遗,非遗在我。
《执念》文风直捷、简朴、明白,书中出现了各种灵性之笔。写徐宁,作者率先写一只黑顶鹤,黑顶鹤轻盈,甘州大地厚重。黑顶鹤经常造访徐宁的梦,所以这篇由“总是”起笔。往后,作者写徐宁如何起身,如何克服人生的重力,出甘州,入甘州。在交巴加布的叙述中,当话头再次转向了父亲时(“我还是想说我的父亲”),作者将接下来的一节重新命名为父亲。作者不但要回观受访者的世界,亦须进入他们所依托的艺术形式之中。交巴加布领作者看到了一幅新完成的唐卡,其中一只猴子骑在白象上,目视前方。作者写道,这只被画出的猴子,率先看到的是绘画者交巴加布的唐卡世界,物我两相观。写许明堂,作者将人物的叙述安置在一场皮影戏中,文章第一句是“看皮影要等天黑”,后面一处闲笔写到一位身穿淡绿色短袖衬衫青年的等待,两种等待同时行进。
甘肃分为陇东、陇右和河西,其中的黄河及支流的渭河、泾河、洮河等流域是中国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。魏晋以降的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更有着特殊的地位,陈寅恪说:“惟此偏隅之地,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,经历东汉末、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,能不失坠,卒得辗转灌输,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,蔚然为独立之一源,继前启后,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。”这片土地的声音常常显得厚重,唢呐、太平鼓、花儿、贤孝等等如是。《执念》正是以此为渊薮,为情造文,书写一地之文明,彰其地其人和其情。在作者的协同下,《执念》中出现了一种“甘肃性”。东西横跨三千里以上的甘肃,很多时候难有一个稳定统一的文化认同。但《执念》中,陇东的唢呐、皮影,甘州的宝卷,凉州的贤孝如同一体,陇人耿介质朴、严谨方正的秉性呼之欲出。“花儿皇后”汪莲莲和众多的盲贤孝艺人不懂文字,同吟游诗人荷马相似。由抒情和记忆构成的传统中,承接了一份古老的记忆和文明。这也是所谓的甘肃性。
《执念》本质上是针对土地的写作,涉及的非遗和滋养它的土地密切相关。在人物口述的头尾,作者会延伸出一些地域风貌和物象,黄土地、黄河、河西走廊、凉州城、莲花山、大夏河、环江等。阅读《执念》像是在巡游甘肃,深入到毫末之中,注视生命本身。在人与艺的背后,是作者对生死、疾病、困苦、振兴,乃至衰败的书写。张晓琴记录下这些似乎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,书写甘肃大地的个人“身在何处”,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。《执念》做到了为民间留史,为厚土传声。


